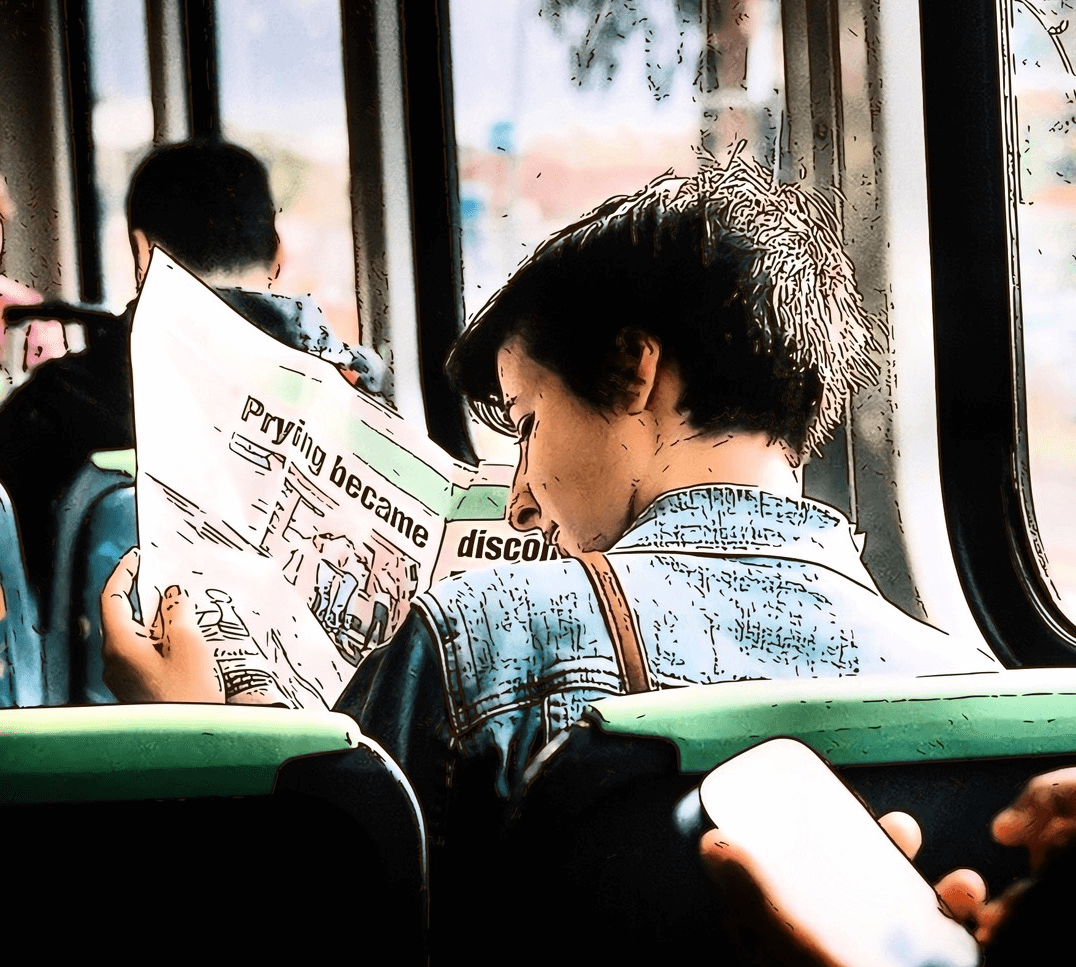按照乔希·维茨金的写法,故事得从那次世界冠军赛说起,今天我们不这么写。
乔布斯曾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做演讲,主题为” Connecting the dots”,他说:“漫长的人生当中,所有那些看似不相关的点点滴滴,会在未来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圈姐(某司PM)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想法是:“这本书看得一种,前30年白过了的感觉”,可能这本书和她的很多体验能够立刻联系上。两年前我看完此书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悟,只觉得和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有很多能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乔希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仅此而已。后来每次在生活中取得一点点进步的瞬间,总会不自觉地回想起书中的话,这样的次数多了,才慢慢体会到乔希想表达的精髓里的一点点。
一般而言,总是要信息汇拢到一定程度,才有作出判断的基础,才有接近真相的可能。
好比写文章,在堆砌事实、经历、灵巧的词藻和细腻的感情之后,才会有写出可堪一看的记叙文或者散文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建立在事先规划的骨架上,也不建立在下笔前的自我期许中,它是在写的过程中,每一次反馈每一次修正每一次再往前一步中反复求得的。基于这个过程得出的结果,会给人一个错误的暗示,觉得好的作品是精心打磨的结果,是一把铁杵磨成了钢针。如果这么看,就会赋予打磨太多的意义,在思维惰性使然的情况下,聚焦于打磨,以打磨为中心发散,基于打磨发展出一套新的方法,然后绕在里面走不出来。其实打磨,只是在接收反馈来的信息之后的下一步,如果反馈给的是修正,那就扭一下,如果反馈暗示是可行的,那就不扭了。在《表象与本质》的结语里,侯世达和桑德尔说范畴化和类比是一回事儿。在这里,修正和不修正,也是一回事儿。
故事写到这里,轮到爱因斯坦出场了,他踹开瑞士专利局的大门,拿着那张写有E=mc²纸张的手激动地挥舞着在空中摆出迷一样的动作,冲出来对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急吼吼地喊道:“上帝从不掷骰子!”
(上帝内心OS:“孺子可教也!”)
当我们说学习的时候,如果加一点天才的滤镜,联想一下牛顿、莱布尼茨这类开天辟地的人物,可能会把学习理解为人物的固有属性(聪明、智慧等)的副产品——“TA就是脑子比较好使啦。” 事实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和我们的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更好地使用了我们的它。
在阅读这个爱好里,如果阅读足够的书目,可能会在读这本书的电光火石间想起另一本书的内容,这是大脑运用类比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场景,也是学习的基本模式。无论学习什么样的知识,都只能基于已知的信息的来理解它,幻想多一点就变成了玄学或者神学的理论,这也与世界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理论上是一致的,理论永远只有指导意义,惟有联系实际并不断进行下一步,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也要改变自己适应世界。这里的类比,既发生在已有信息和新的信息之间,也发生在脑海里与现实中。
回顾这些年来读过的书,和写过的文,每一个觉得有成长的时刻,都不会有理所当然的感觉,也不是自己虚构的理论得到证实的结果,相反,它们都是我不断基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在特定具体情况下与那个具体的场景磨合的结果,在当时可以有那么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种感觉远远不是终点),在下一次时,就能基于前者作出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可能带来的感受不那么积极,也可能很积极,之所以不那么确定,因为预测的时候只有我自己,而没有具体场景。
晋朝皇帝司马衷听到臣下说百姓没有粮食快饿死了时,问:“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在司马衷自己的场景里,没有米饭,可以吃肉。可由于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有意识地忽略)没有米饭也没有肉吃的场景,问出来的话其实代表了他的正常判断。
在学习中,这种对场景的敏锐反应,反映为对节奏的把握。乔希在太极练习时,能通过对方腿部的微小动作,感受到下一步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就像他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能即时根据对方的布局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是在作出对比类似场景实训之后的结果,这种对比的基础被梁宁称之为高手的微观体感,我觉得也可以称为感受力,感受力是可以习得的技能。
学习的精髓在于类比的话,优质学习的本质就呼之欲出了,不是类比的次数,而是类比的质量。通才如达芬奇,大概能以优秀的感受力为基础,敏锐地在不同领域里找到联系。(这里的联系是范畴化,也就是类比,见《表象与本质》结语)
很多人认同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也喜欢说细节决定成败,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喜欢以性格为借口寻找不可能。阿德勒则认为人是有意识的个体,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性格不是命定的,天才也不是天生的。智慧也好、愚蠢也罢,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结果。外在属性差异都是内在学习方式差异的具象体现,所幸,我们拥有的是同一个生物属性的大脑。技能的习得和性格的改变,都是学习。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能以新的视角看下面这句话了。
牛顿说:“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