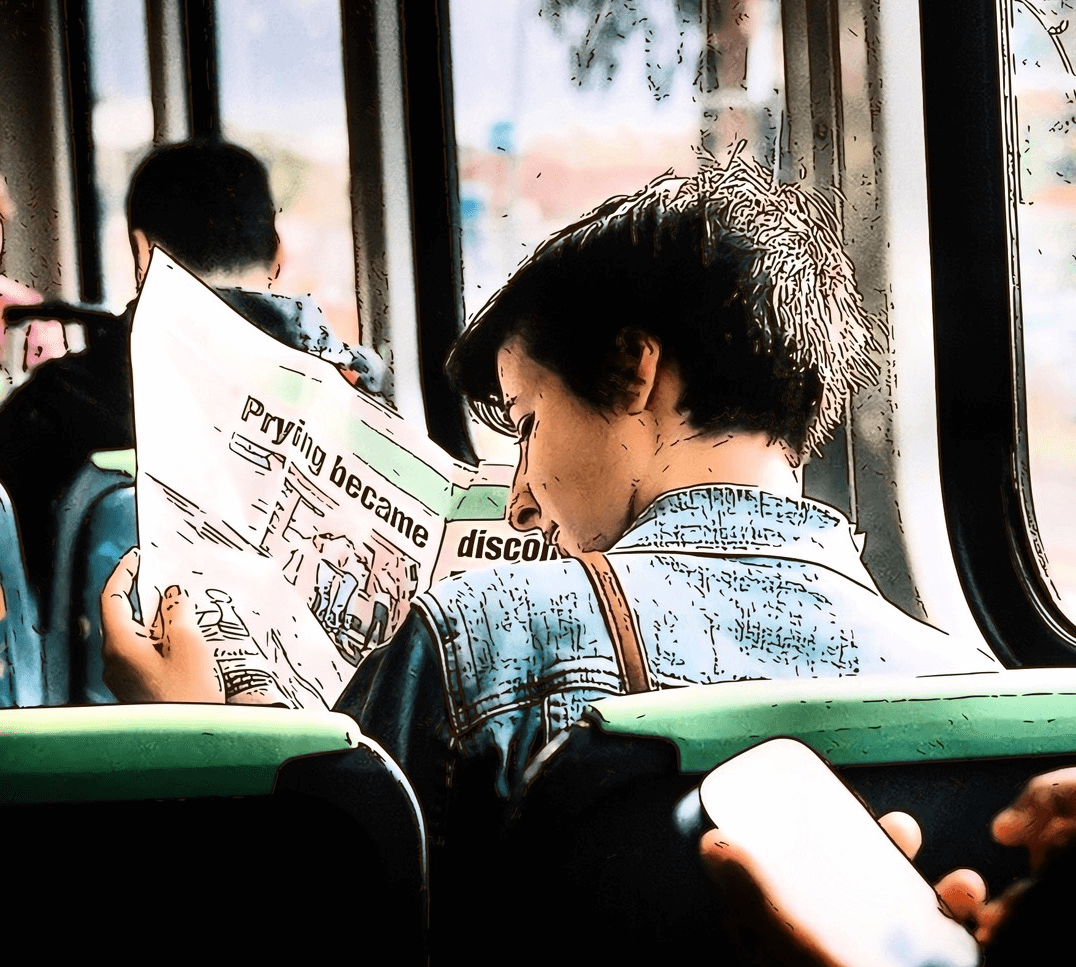小霸王买到了,旋即也被君上大人们雪藏了。
接下来的时光里只能抱着小霸王去其它小朋友家打游击,或者去吃霸王食,但霸王食可吃不得多,会被群殴。或许是因为彼时活得凑巧比较认真,时光啊是在慢些儿走着,一点加速也不带,不像现在,稍微闭一下眼,不知道是多少个年头后了。
那么,到了PC兴起的年代。住在学校里唯一的好处体现出来了,可以混进学校的电脑室玩点不一样的东西了,比如「帝国时代2」。1990年代,家用个人电脑尚未实现比尔盖茨一人一家一电脑的愿景。
帝国时代2对于现在的05后手游玩家们可能属于比较陌生的游戏类别,即时战略。初始阶段略等于种田,同时可以发展单位“探索大世界”,发现并收集资源,规划科技和建筑物发展;侦查敌方单位,探得对方发展情况,干扰其正常发育,乃至决战。即时战略里没有前中后期之分,它的精髓在于real time「实时」。
在一场典型的即时战略游戏中,占有更多资源的一方,能建造更多的战斗单位和建筑。这些资源通常分布于地图上的特定地点,或占有/占领以被争夺为目的被地图制作者分布在地图上的特定单位或建筑。更具体地说,在一场典型的RTS游戏中,玩家可以收集资源、建造建筑、发展科技和控制战斗单位等。
我的RTS“生涯”起源于在晚间只露出微光穿过不小心的窗帘到外面的学校四楼电脑室的帝国时代2,发展于网吧里和小伙伴玩得昏天黑地的红色警戒2,终结于大学宿舍里的被二狼虐得体无完肤的魔兽争霸3。中间也玩过第一人称射击如反恐精英、黑鹰坠落,碰过休闲游戏譬如糖果粉碎传奇、泡泡堂和跑跑卡丁车,终于是落到角色扮演游戏的大坑里走不出来了。
二狼在魔兽争霸的世界里把我杀得连妈妈都不认识了,我只好去魔兽世界里秽土转生(避避风头),二狼这混小子也来了,还选的是牧师,这么会给自己续命,看来我是没机会报仇了。
角色扮演游戏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玩家可以把自己代入游戏世界,体验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有的话),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强。它是无时无刻不在与玩家互动的,或者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玩家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这种互动的情感体验如此强烈(尤其在最开始),以至于会让有的玩家沉迷其中,以至于现实中有意思的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这种内外身份的转变,除了游戏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在于玩家自身与现实世界的连接在有趣程度上的多寡。换句话说,觉得现实生活不那么有趣的小朋友,更容易对游戏产生依赖感。
从暗黑破坏神2到传奇到QQ幻想,到艾泽拉斯,到海拉鲁大陆,这个旅途开始的部分,总是差不多。慢慢探索,缓缓观察,接收引导,熟悉这个世界,完成某些任务,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源,变强,然后继续继续下一段旅途。单机角色扮演游戏,可以很好地把握这个叙事结构,不会变得很拖沓,不会被长线运营劫持,被迫讲一个一次又一次无限续杯的故事。长线运营的游戏很难把握这个节奏,总是为了顾全故事以外的因素续写剧本,可惜,没有结局的故事不是好故事,魔兽世界运营了快二十年其故事线已经是一团乱麻了。
在童话故事里,公主与王子在战胜恶龙之后,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happy ever after)。要续写这个剧本,需要有创作全新的故事的觉悟。具体的方法可能有差异,但王子公主们,肯定不会是从那之后就一直无忧无虑幸福生活着的,那样下一个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就没法起头了。在前一个故事里,为什么结尾会有那样的旁白,因为所有真正与人物产生了共情的群体(观众、编剧乃至剧本里其他人物)在经历这么大的艰险之后,当然会毫无疑问地坚定相信,从此之后的生活一定是美好的。如果没有这份美好的愿景,这整个故事从开始就没有什么意义,故事里每个人的付出和奉献都成了笑话,且一定会让他们发出灵魂拷问:“我为什么而来?”
唐僧出场了,“所以呢作妖跟作人一样要有颗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而是人妖。“
在玩角色扮演游戏初期,我总是想要更炫酷的装备,更快的升级速度,并处于一个更强力的队伍中,和我在人生初期想要的东西一模一样。这种比较级的“更”,它的评判标准类似于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包容整个群体的价值判断。作为最大公约数,它本身必然会得到全体玩家群体的认同,至于它是不是作为单个玩家的我所想要的全部,这很难说。
在游戏、生活和学习道路上的孜孜求索,本质上差不了太多。不同之处在于:在游戏里,可以开人民币外挂;在学习中,这个外挂不起作用;在生活中,开得起人民币外挂的是已经不需要外挂的人。
在这个悖论里,只有没钱的和学习能力不好的玩家才会使用人民币外挂。根据使用外挂的目的,又可以分为:适当使用外挂补足因游戏理解不足带来的游玩困难,以及在对现状不满的前提下为了某种饱腹感使用从而获得即时满足的外挂使用。这两种(或者说所有)使用方式的目的都是玩家基于自己当下的游戏境遇作出的选择,它们也是玩家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境时会做出的选择。两种选择的结果虽然是一致的,带来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前者是坦诚接受失去的价值,欣喜地接受新来的满足;后者则是痛心于失去的价值,固然短暂的欢愉会带来无与伦比的观感体验,失去的价值却一直在失去并且永远被缅怀,似乎由于痛苦的存在,那份失去的美好变得永恒了,一个阴影,永世的牢笼。
单机非多人合作游戏需要的程式外挂,可以自己制作或者购买,通常不需要太多人民币,可能这也和单机游戏一次买断,没有日常性维护有关,游玩基本属于一次性有关,各方面成本都比较低。
故事没有结局,被无限拆分,玩家就需要继续游玩,继续花钱,继续为厂商献上自己的腰子。没有结局,编剧无法写出好故事,就只能水剧情,或者开支线(平行世界),这样挖的坑越多,最后需要埋且理清的地方就越多,最后的最后编剧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圆起来了,只能草草收场。比如,在「冰与火之歌」里,让龙母突然变成被仇恨冲翻头脑的疯女人,把所有矛盾点推到龙母身上去,龙母成了把这一切混乱斩断的”契机“,再通过私生子对龙母的击杀让故事回归权力斗争的大舞台。龙母本身的形象,其一直以来的人物塑造都清楚表明,她不是一个行事冲动不计后果的疯子。雪诺确实合理地走上王位,深刻契合了原著「权力的斗争」的主题,可转折的生硬以及人物匪夷所思的行为,让整个故事彻底崩坏,两位大编剧(这两位接下来要拍奈飞版「三体」剧集)赢得一片骂声。
在影视作品里,主角总是成长迅速的模样,ta所经受的那些必经之路,即使是被很夸张的演出表现出来,加起来在一起也没有多长(现实)时间,不会成为观众关注点里哪怕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作品中,主角的成长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困难的阶段)都会被极速带过,一段很励志的BGM配上主角朝气蓬勃的磨练过程,把整个成长过程至少描绘得足够简单,也会被读者潜意识地认为很简单。
在现实的角色扮演游戏里,一个普通的玩家则必须在现实时间里经历漫长的养成过程,从空白开始,通过任务、探索、打怪、谜题等方式获得资源来支撑成长曲线。由于几乎所有在线养成游戏都含有概率获得要素,我觉得可以统一把它们称为Gacha游戏。概率获得,表示有的人可能第一天就获得了,有的人可能版本结束也获得不了。
在现实中,这类有着无与伦比运气的人被称为欧皇,由于他们人烟稀少,并且通常发生在某个遥远的角落,陌生感拉开的距离在心理上只会更远。在线游戏则不同,由于本身的虚拟属性和网络社区的方便程度,游玩同一个游戏本身就能来某种性质的社区属性。百分之零点一的概率在海量玩家群体面前也不会显得多么罕见,加上幸运儿玩家在获得喜爱之物时的分享冲动和社区到达的便捷程度,都能在玩家群体之间促发某种程度的共鸣。在现实层面的影响会变成,“似乎在里面成为欧皇也不是太难”。
欧皇是可遇而不可的,偶尔的欧皇也不会是永远的欧皇。概率学的尘埃落下来,每一个人都是版本的眼泪。绝大部分人(比如我),正确的做法是老老实实在里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玩,不要梦想掉下悬崖获得绝世武功的秘籍,绝大多数的我们的生活经验非常现实且接地气地提示着我们,作为普通玩家不要做黄粱美梦啦!
经历游戏初期井喷式的小奖励之后,玩家们很容易陷入惯性思维期待更多奖励,这是多巴胺的固有刺激节奏。作为经营者,厂商则不会那么如玩家所愿,游戏制作是为了赚钱,营造良好游戏生态是为了可持续性赚钱。当奖励的狂潮落下帷幕后,玩家们的策马狂奔的需求与微小福利间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对玩家,这就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果无法接受这种前后落差,要么就弃游走人,要么就捏着鼻子继续玩。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捏着鼻子继续玩的。当然,不想玩了和捏着鼻子继续玩之外,还有第三条路,承认现状,继续玩下去,并且从当下的游戏体验中获得乐趣,这是少有人走过的路。
在游戏初期,是炫酷的战绩、游戏人物的等级、装备和属性在吸引着我投入其中。玩传奇的早期阶段,如果当天玩过该游戏的话,睡前,那个法师都会自动出现在我脑海中,对我说,快来升级啊,你的宝贝要二十级啦!
这魔力是那些没有此类游戏体验的人难以想象的,大概是美食之于吃货,好书之于书痴。可惜,新鲜感总是在最初的相遇之后很快消逝,徒留一片唏嘘在人间。
与其它宝藏不一样,这种欢愉是寻找不来的。它只会在自己想要的时候才出来,换句话说,它和欧皇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些游戏教给我的事里,如何应对这种对欢愉的饥渴感贯穿了始终。
创新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创新无法成为无根之源。即使是人类文明的初期,也是在积蓄了足够多的素材样本之后才完成最原始的创新的。对石制工具的创造性应用,建立在无数次用石头砸核桃的过程中的一点点不同想法,也有可能来源于人类观察其它生物对作为工具的石头的使用。一切的创造都以之前的创造为基础,所有的创造都是想法、练习和对实体的不断改造联合起来的产物。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每个人的创造都是在对前人经验的复制粘贴基础上的随机组合?
在前文(第十三段)的悖论里,之所以出现没钱且没有学习能力的人却会话费相对其生活水平较高的金钱购买游戏外挂这种事情,因为理性变量可控,有些变量却不是可度量的数字,尤其在这种变量被视为毫无意义而时常被忽略的情况下。
在这个框架下,饥渴感成为了广大变量之一,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变成了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在传送甚广的四象限时间管理法中,可以按照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和不紧急不重要来管理时间。我们知道,由于变量的存在,产生了本文第一个悖论。
现在,另一个悖论要来啦,由于与第一个悖论里的变量多少多少有点关系的另外一些变量,时间管理法的实现是很困难的,而真正能高效管理自己时间的人,很少听说他们对自己的时间管理法有什么头绪。现在的这个悖论,就变成了:
时间管理法的有效性堪忧,真正有效能管理时间的人不需要时间管理法。
有些大人物喜欢谈延迟满足感这个概念,似乎,把当前的追求推迟到一定时间后,是一种很优秀的能力。虽然很多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科普书籍,都把延迟满足感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加以表述,这个概念是错的。满足感在人的体验那个范畴里,是主体还是客体。这样问或许有点复杂,简单点,满足感是真实存在的吗?更简单点,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在人生的路途中,终点是真实存在的吗?
更简单点,游戏世界里,存在终点吗?满足真的存在吗?
玩过游戏的老鸟都知道,如果游戏的故事是没有终极结局(故事完全结束)的,那多半只能玩养成这条路,让玩家们以角色养成为目标,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开发者就可以只需要改代码加等角色等级装备数值就行。偷懒,但是一段时间内有效。如果没有故事常年无法完结,长草期又没有自己能设定的目标,那这破游戏多半是玩不下去了。这也许稍微能说明一点,游戏世界里也没有终点这一说。
延迟满足感正是建立在这非终点基础上的“终点”,如此“终点”非终点,此“满足”也非真满足。
在Gasha游戏里,有一类被称为囤囤鼠的玩家,会囤积若干个版本的所有抽卡资源,只为在自己喜爱的角色出现在卡池时梭哈,偶尔,也会有玩家连卡池也不碰了,在长久寂寞且孤独的等待中,他们爱上了自己攒下的原石。
如果这是延迟满足感的话,很大一部分(不是全部)玩家,在搜哈完所有资源获得传说中梦寐以求的角色后,获得的满足感是巨大的,也是短暂的。若非真正能从游戏中获得乐趣而不是从某个非变量目标中获得乐趣,玩家们总是会需要不断寻找下一个目标。毕竟,在没有目标的黑暗森林里,有lost和empty这两个更可怕的东西。
那些游戏教给我的事情里,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自己创造出对游戏的热情,不是依靠厂商对游戏的更新优化,不是依靠外部力量改变带来的变量造成的变化,也不是从PVP、PVF的混乱秩序中获得某种存在感。这和生活中某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寻找,那些东西一直在我们身边。
是的,如果这里没有变量,你喜欢的是玩游戏过程中的自己。
恭喜你,头号玩家!
作者一生与技艺和风格的纠缠,是一种可观的、有时间分量的努力:探索我们思考的事情,我们在乎的事情一一我们是谁。
——埃米莉·希思坦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