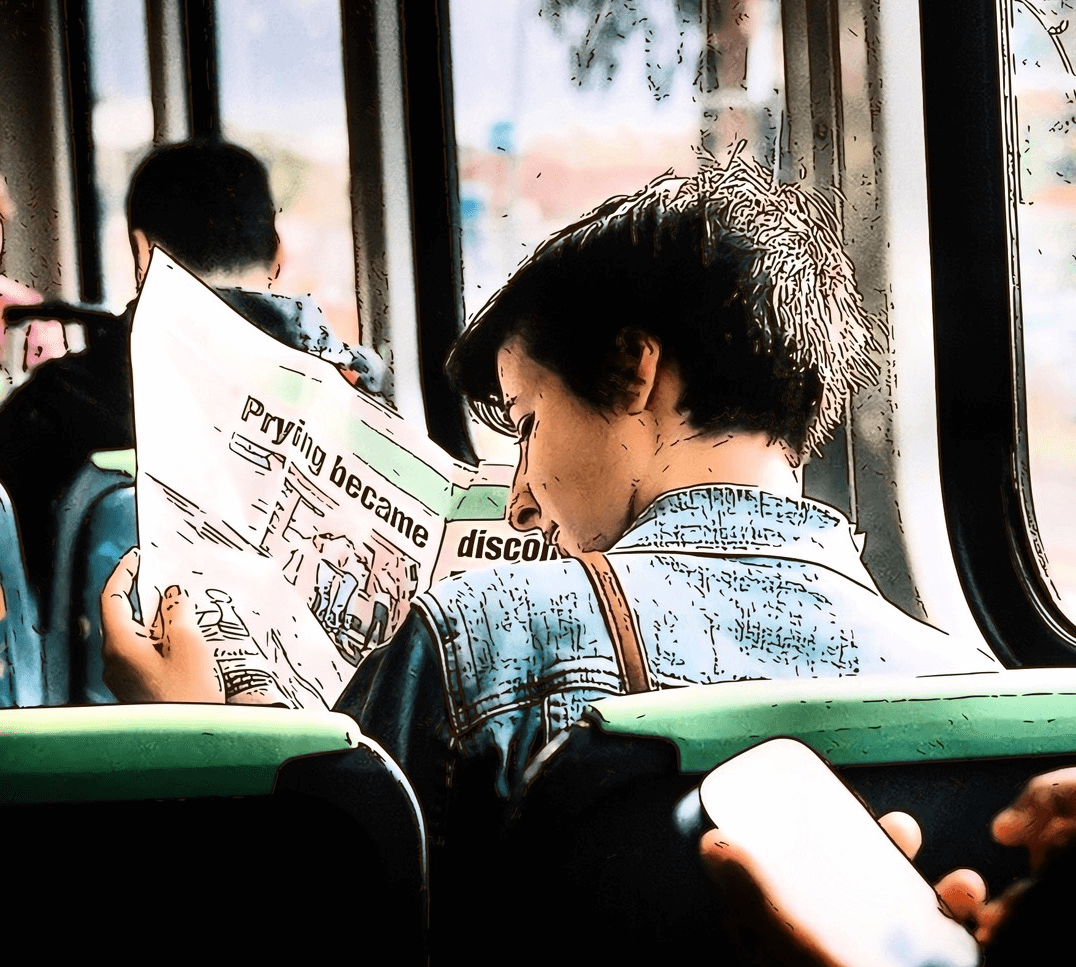徐振贵教授于2006年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认为《论语·述而》篇第二十一章“子不语怪力乱神”应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夫子停止不说了,唯恐分心用力影响了凝神思考。(原文是:“孔子不说话了,惟恐用力分散影响集中精神”。这里用一个更雅致的释本)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
与此相对,传统上受到认同较多的断句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孔子绝口不谈关于“怪异、暴力、悖乱、灵异”等事,以魏晋时期著名经学家王肃为代表。另有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记载了另一种断句方案,即将“怪力乱神”作“怪力”、“乱神”两件事来解释。按照徐教授原文的意思,“子不语怪力乱神”卡在这三段中间,只有解释成他“新解”的那个样子,才算“文通字顺,语意连贯,符合孔子的为人”。
如果用文通字顺、语意连贯做《论语》解释的标准,在更大的尺度上,徐教授可能不一定对。先说对待鬼神的这件事,《论语》全文有两处描述分别是: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雍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两处摘录都以孔子言论的形式表达了对鬼神的态度,倾向十分明显,这里与徐教授的看法并无明显冲突之处。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言行为主的言论汇编,在古书中又别以论、语、传、记等字单称,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论”通行的读音为(lún),为论纂、编纂的意思,“语”为谈说的意思,如《国语》之类,合起来指言论的汇编。
—— 维基百科
以语录为载体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在形式上是以记录来表现孔子所言所为,通观全篇,只在《论语·乡党》篇第一章有最接近内心活动的描写:“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这是由外在行为“恂恂如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推论,推论的结果指向的也是客观行为“似不能言”,无关内心活动,《论语》全篇就没有直接描写内心活动的,观点看法都以言行表现。徐教授联系附近的上下文把“怪力乱神”直接翻译为孔子的内心活动——“惟恐用力分散影响集中精神”,在更大的尺度上能否说通,有很大合理怀疑的空间。
忘了初见此句是在什么时候,现在碰到这句话会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是:李慢慢独自面对悬空寺首座,首座坐在莲花上口诵佛号,漫天神佛充斥整个空间,目力所及之处都被金光染黄,云朵消失不见,身前身后都是咒言,是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修罗场。李慢慢的表情和平时没有区别,他一字一顿,似有千钧之力,又似浮在白云上,念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神字,所有的光芒万丈瞬间退散,世界之大,只留下站在悬空寺前的李慢慢,微风吹起鬓角,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还会有其它的画面,一般都很古风,有时候是在灿烂的星空下,有时候是在无边的沙漠里,有时候是在华山之巅,有时候是在宫城的朱门红墙外,依据本人所处的情境发生改变,但无一例外都很美,即使是我站在中间的话,估计会吓尿,就很美。
所以和好友在老闸北某个交通不太方便的电影院一起看上影节侯孝贤的4K《海上花》时,我和友人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一边觉得美美哒,一边又像看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除了电影场景里的斑驳光影,竟然还看出了一点秦淮河畔的味道来,明明是很艳丽绮丽的遐想空间,硬是被挤出了一丁点“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的纯粹(这个感觉是王老爷给的)。
一首诗做成之后,不是就变成个个读者的产业,使他可以坐享其成。它也好比一片自然风景,观赏者要拿自己的想象和情趣来交接它,才能有所得。他所得的深浅和他自己的想象与情趣成比例。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切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没有创造就不能欣赏。
—— 《谈美》朱光潜
几天前第二届《中国诗词大会》武亦姝613分上清华的新闻刷屏,坊间评论有分析爹地背景的、有哀嚎教育不平等的、有羡慕别人家孩子的。这些不同角度代表了不同人群最倾向看问题的方法,无论此中角度多么刁钻,他们一定能在里面寻找到与他们自我认同接近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论,也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就好比,热爱星座学说的人总是能用各种理由让自己对星座论怀有坚定的信念,此前我总觉得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后来发现不可理喻的是我自己。这类人是在星座论和表达对星座说的认同里,寻找他们自己,去跟他们强调星座论是结果主义导向的自我暗示,这就好比跟一个人讲:“你快说,你自己是傻比。”(对星座学说无任何偏见,说暗示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不一定对,说一定错也可以!)
他们说得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最卓有成效的角度看,倒是有事实可供参考。
当年只是单想学好英文的时候,天天看Economist和NYtimes(现在推荐看WSJ),看得眼冒金花头晕脑胀。后来某一天,忽然觉得英文很美,爱上了北美腔说英文的感觉,后来又知道了背书的学习方法,很简单,很难坚持,但背书的时候就觉得很美,张开嘴觉得自己像个沙雕,还是会跟着安迪·克雷格学习北美腔调,慢慢就更加能感受到这门语言讲起来的韵律之美。这是很直观地对美的认知,具体哪一天不知道了,大概是大三左右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道光照进来,一种无法言说的美。
张三丰教张无忌剑法时叫他忘招,像是叫他从无知到有知,再从有知到无知,乍看起来挺让人困惑的,换一个词就明白了,返璞归真。
从小我们就不断接触茫茫多的信息,所有人都在教我们做人,刚开始的我们看不清,觉得他们说得都对,后来,有了一定的信息储备,我们又会觉得他们不一定对,我们的大脑需要锚定点(anchor , 见<Thinking , Fast and Slow >),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各种理念各种论证,并把找到的能说服自己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然而大脑只能根据已有信息来构造我们的认知,如果觉得自己的大脑已经装下全部需要的知识,我们就会把自己撑住,撑住的可能是神佛、鬼怪,也可能是旧爱、新欢,但这都不是全部。
科学作为一门学问,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像照妖镜一般闪得自满的眼睛目不能视满地找牙,每发现一个理论,就会发现更大的未知空间。既然永远也没法发现事情的全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给心上打开一个豁口,让光照进来。
光照进来的同时,美才能进来。
坚定信念听起来好像是坚守一个理念毫不动摇,如金字塔版屹立千年不倒;就像人言所谓学习,一般都指吸收积累,内化天地之灵气,而你在石中等着蹦出来去抢龙王的定海神针。我觉得,相比聚拢,更像是不断地有选择性地抛开,当然,不断抛开的前提是在不断聚拢,这是一体两面,抛开只是更有决定性的那一面。(聚拢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即使是一个生活最“死板无趣”的人)
“子不语怪力乱神”,初次看到的理解是——夫子才不说妖魔鬼怪这等俗事;后来变成了——不以正道在心要为鬼神所制;李慢慢一字一顿念出来的时候,理解是——愚蠢的怪兽啊,接受神力的惩罚吧;看到徐教授的解释时,想法是——夫子慌不择路了吗?
朱光潜说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它有两个要素:一是独立个体间适当的距离,从前觉得最好的关系是没有距离,现在觉得最亲密的爱人必然会有一定的距离,这并不是不美,这才是自然的,就很美,也给了自己信心;二是以极为专注的姿势以至于物我两忘,这句话引申出来一个问题的答案,若问为什么生活如此无趣没有美好可言,回答应该是,因为从没有认真生活过,这里的认真可能和一般意义上的认真不太一样。
李慢慢停留不惑境十五年,日印手掌上下山门,朝入洞玄暮知命,再三日越五境而无距。在无距这个境界,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呢?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 《兰亭集序》 王羲之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 《观沧海》 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