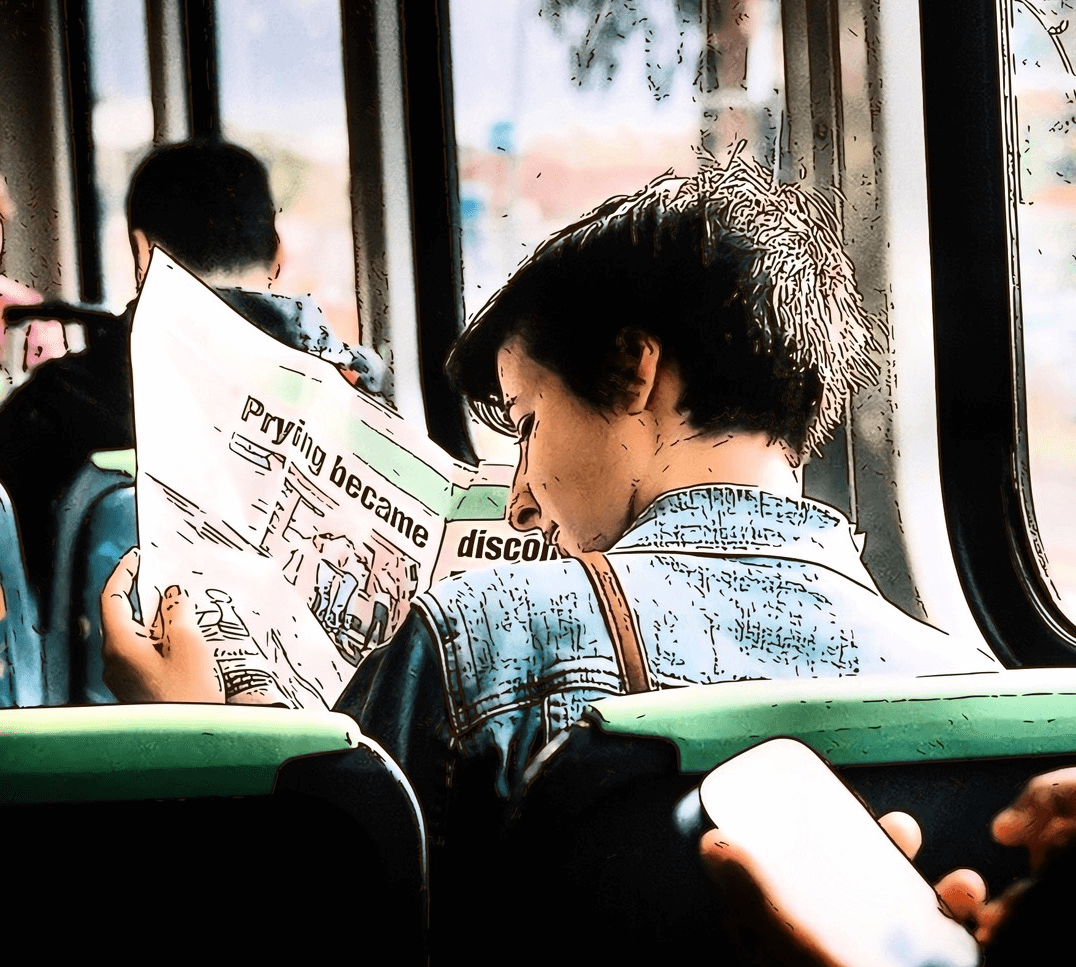绝対在日语里的发音用罗马音写出来,是”Zettai ni”,喜欢看日剧的朋友能经常听到这个词。
在日语里这个词的意味,有作为形容词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也有作为副词的“绝对地”,都表达了无条件必须做到的“绝对の意味”。同时,作为一个形容词,它也暗含了相反的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如果要加上一定的感情色彩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结局是命定的“主角”命定的“命运”。
在英文中有一个被经常遇到的词组:“what if ? ”
What if we could make a miracle ? What if we guys could build a future in our hands with our own efforts ?
“what if”最美妙的地方在于,他建立起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不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可能性。假如真如某些书籍所言,一万小时练习可以造就专家的话,这种为了成为什么而练习一万个小时所成为的专家肯定没那么有趣。勤奋、坚持这些都是对现象的归纳所提炼出来的品质,语义学上的归纳是一个大框,他总是以最大公约数作为整体认同的前提,是以各种其它细节被牺牲被掩盖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一个人善良的、以为他人幸福为目的的好人,表现出愚蠢就丝毫不意外了。总结出的现象总是片面的,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则是在三百六十度无死角,以一种连续不间断性持续地展现着自己。一个善良的人,Ta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一个单一的思维模式,除非ta的神经冲动都只往一个方向传递递质。
根据目前已知的脑科学研究成果,神经冲动的传播和大脑神经链接的建立一样毫无规律可循,只从一个节点往另一个方向传播,这与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神经脉冲的天性是不符的。
既然一个理想意义上善良人的思维方式,不是唯一不变的,那Ta就从一个只被看见时做好事的善良人变成了一个被别人所看不见的时候也无时无刻不在做好事的人了吗?或者,Ta确实一直在做好事,并且也一声称自己在做好事,但因为没人看到过,Ta就不算好人了吗?
一个不绝对的好人,绝对是绝对的非好人。这一逻辑前提建立在“好人”——这一被抽象被归纳的“品质”,能完整代表并解释一个人全体外显行为的逻辑结构。即,因为Ta是一个好人,所以他的所有/全体行为都必须是“好的”。依照此种逻辑,一个受害者之所以能成为受害者,Ta必须是“完璧无暇”的受害者。一个好人,做了一小件不好的事情,就成了一个非好人,一个非好人,那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从这个伪命题的逻辑,能得出的只有:已知A是傻逼,所以A是傻逼的诡异结论。一个傻逼必然是纯粹的傻逼,百分百纯天然的傻逼,一点有逻辑的事都做不得。我们当然知道,一个傻逼,还是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这点清醒,不仅是理性的认识或者常识使然,还因为那种疯子通常我们碰到过或听周围的人说过,我们给他们建立的画像本就是与一个被归纳出来的“品质”不沾边的。
一个好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语境下,则更像是一个想象的概念,赞美Ta不仅仅是出于我们的本心,也在于我们所寄托的希望这个好人能带来的”改变“。热切的期望总会带着不切实际的妄想,太想要所以忽略其它细节,所以渐渐觉得这个幻想不再遥不可及。这个时候,好人就会遭殃,他但凡是出了点差错,就会从一个好人蜕变成一个不坚定分子,一个修正主义者,一个叛徒,乃至一个敌人。从一个万众景仰的偶像,变成一个遗臭万年的罪人。
每个人会犯错的人,在这个伪命题前,都会成为受害者,有人从来不犯错的吗?
使理想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是持续的正反馈和随之而来的正面心理暗示;把理想埋葬的根本原因则是无数次一脚踩空的无力感和无数次踩空带来的无法前进的困境感。没有理想或者说没有目标带来的感觉有所不同,那种在浩瀚的空间中的迷失,中文很难描述,用英文单词的话倒是可以很好地做总结:empty.
根据牛津英文词典,emptiness有九种含义,这里取比较常用的三种:
- the state of containing nothing. “the vast emptiness of space”
- the quality of lacking meaning or sincerity; meaninglessness. “he realizes the emptiness of his statement”
- the quality of having no value or purpose; futility. “feelings of emptiness and loneliness”
在影视界的童星场,年少成名的幸运儿,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名声与财富面前,总是容易陷入迷失与空虚,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剩下的那点自我空间,迅速被emptiness填满,说是填满,其实填满的东西也空无一物。原本空白的,被实心的兴奋、激动和强烈感情盛满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被环绕的各种感受冲击。经年累月,这些冲击不再是冲击了,或者它们还是冲击,只是不再是“冲击”了。这一刻,这张白纸上的作画,被橡皮泥擦了个干净,但众所周知的是,橡皮泥是无法完全擦干净白纸的。那些被作过的画,那些用在作画上的努力和汗水,会以特别或不特别的方式留下来,比如痕迹,比如作画的手与纸张摩擦时留下的汗水。
此时,他们再也回不到那个什么也未体验到时的白纸状态了,那些曾经饱满的记忆会吸引着内心不断索求能再次点燃内心的素材。有人总是询问,何时能再找到属于自己的儿时的快乐,众所周知,快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状态,可遇而不可求,就像欧皇一样。
也有可能,再次找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原本的感觉,而是一种一直被回忆和再创造不断重塑的记忆。这些记忆经年累月,也变得和之前的经历一样成为了新的黑洞,它们成为了一场演出的两个主角,互相塑造也互相重塑。
结果就是,几乎永无止境的相互折磨。寻找,兴奋,感觉不对,失落,混乱,再出发,寻找。在这个循环里,没有任何最终赢家,在此端和彼端大家都很失落,都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且永远也找不到。
因为这种所谓对的感觉,根本不存在。
它只存在于对过去的想象中,甚至到最后,和过去都没有一丝一毫关系,变成了集所有美好于一体的幻想乡,一个桃花源。
一个桃花源,它不好吗?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