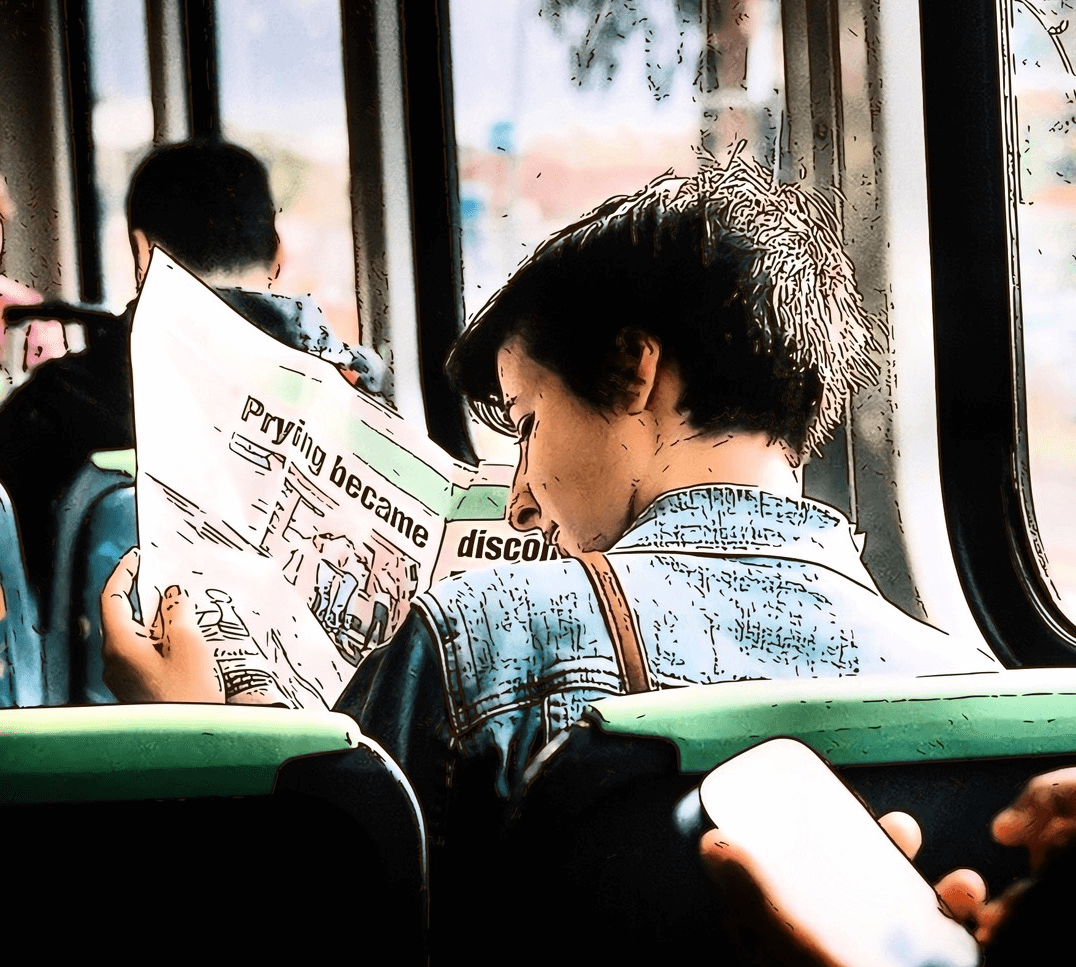心仪很久的暗绿色菱形方块修饰不锈钢保温杯到手之后,自带杯优惠配合某咖啡店工作日七折折扣的月卡,让魔怔人如我下午不去买一杯美式会觉得自己在亏钱。
意式太浓有点受不了,美式刚刚好,越苦越好,喝到后面,仿佛有这稍许严厉的味道才会有咖啡的感觉。拿铁、馥芮白或卡布奇诺,都很好,不过不是我喜欢的好,而且用杯子装美式,不用在喝完之后用洗洁剂认真做清洗,倒进热开水喝完就干净了,这实在是太极简了。
住在解放碑的好处,就是能听到不远处也许是朝天门码头传来的整点钟声(不确定是哪里),这种古早味的荡漾感很厚重并不扰人,反而令人心安。与平时不同,跨年的时候钟声在凌晨十二点也响了起来,从住所阳台朝解放碑方向看去,可以看到很多人撑着雨伞围在那庆祝新年的到来,看往年视频会觉得今年人太少,新年的氛围却没有少很多,是满满的新年感,是充满希望的味道,终于,终于,终于和充斥着各种酸楚的2022年告别了,新的一年,只要是新的,一定会更好。
钟声敲过十二点的最后一下,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在这何伟写过的江城生活了好一段时间,虽然跑遍了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却并没有偏离主城区,没有去涪陵师范学院看看,也没有往两年前他曾任教的四川大学去过,我似乎被困在了这座城市里。
城市里的好处,是无处不在的咖啡馆,副产品是文化氛围各异的室内空间,和它们的音乐。在这样的舒适圈里,就很难让人产生出走城市的想法,大自然从亲切的陪伴变成了陌生的非舒适区间,成了一个符号,一种向往,却再也不是现实了。彷佛置身在山林间,山林却突然向后极速涌过,离此地而去,留你在一片雾霭尘埃中,不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不知道该迈出哪一步。
咖啡会消解这种无力感,它会在耳边做提醒,告诉打工人脑子要清醒点,滚回去做正确的事。
由于某种奇怪的习惯,我的饮品名单里只有白开水、酸奶和美式。白开水是日常,酸奶是睡前不会导致糖分过量的营养品。咖啡虽然被当作日间的催化剂,被饮用却不是在最紧张最累人的工作氛围中。多年的咖啡饮用也许是磨灭了它的提神醒脑功用,它变成了闲暇时间最好的催化剂,让人更享受舒缓的催化剂。就好比现在在我斜左前方与我面相而坐的小朋友,我们分享着这一张大长椭圆木桌,ipad是让他闲暇时间精神集中的法宝,小朋友已经连着两个小时盯着pad一眼不眨、一动不动了,他变成了一座活着的丰碑,如果一直下着雪,明天早上丰碑会变成冰雕吧,这可就没法永垂不朽了。
如何度过所谓的“休息”时间,曾一度让我觉得是个伪命题。对曾一度自诩为“奋斗逼”的我,休息时间当然是要在上无数的自习、学无数的课程和进阶无数的专业技能上面。这些想法像预制程序一样,在面对类似情景时做出机器人式的应激反应。在强度上,可能已可以比肩工作状态时的强度。
工作多多少少带了点强制的意味,最少最少也有一点点不得不做的悲怆,打工人自己的时间就只剩下二十四小时中除睡眠、工作之外的那点。在我的世界里,这点时间是工作日的七小时和节假日的十六小时。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我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有这么多。在过去的大多数年月里,它们都如潮水涌回海面一样消失得异常迅速,也如平静的海面一般,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
很荒谬的,在现代教育系统里,最起码在我国的现代教育系统里,自己的时间被当作是奖品,也被理解为补偿,成为了学习的对立面,也居然成为了学习的目标,变成了学习的理想结果之一。
有一个美国商人坐在墨西哥海边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和一个刚捕鱼回来的墨西哥渔夫聊天,他问他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抓到这些鱼?
渔夫说,才一会儿功夫就抓到了。
美国人再问:“你为甚么不呆久一点,好多抓一些鱼?”墨西哥渔夫觉得不以为然:“这些鱼已经足够我一家人生活所需啦!”美国人又问:“那么你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在干甚么?”
渔夫解释说:“我呀?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儿们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过得惬意又忙碌呢!”
美国人是哈佛大学企管硕士,他热心地帮渔夫出主意,教他如何不断地经营扩充企业。最后他告诉墨西哥渔夫说:“十五到二十年后,你就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到那个时候就可以退休啦,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儿们玩玩吉他!”
墨西哥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有很多种解读,我觉得解读得都不怎么好,与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最美的风景,不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常见解读一样,都以句中最明确存在的锚点为立意基础,而忽略了点与点之间密切联系的那部分。关于这个故事,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在讨论该追求做“奋斗逼”还是努力做“平凡怪”,也有强调应以每一刻的选择自由为目标的讨论,即随时随地都能做自由选择,而不是只能在限定范围做选择。后者虽然提到了“每一刻”这个重大隐藏线索,本质上还是如欲从心所欲,必先打破这天地那一套。你必须先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解放自己,此时此刻在目标达成前是无法自由的。
学生时代最大的盼望是放假,因为学习本身无法提供自我实现的现实因子,自我激励只存在于对远大理想——“即更好的学校更多的机会”的无休止追求中。在每一次考试后分数公布的瞬间,”理想之神“会短暂地现身人间,赐予对她心心念念的学子们一响贪欢。在这醉人的欢愉中,在众人羡艳的目光里,在深觉枯燥的日子间,她过于美丽炫目,让人流连忘返,一旦抓住了就不想放开,会害怕失去,伊甸园的珍宝变成了被美好和恐惧包装的毒苹果,远大理想也从生活里诸多目标蜕变成了唯一目标。为了持续拥有这倏忽即逝的幻梦、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握不住的沙,理想的少年啊,他变成了偏执狂。毕竟,只有在想象出来的白玉京,永无止尽的运动才会静止下来。
很难说偏执狂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那么,和世间所有的多义词一样,他既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斩对手,斩自己,斩一切活物。
以生物学的角度而言,内啡肽与多巴胺都能带来快乐舒服的感觉。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效用产生于期待奖赏,而不是获得奖赏。多巴胺≈ want,所带来的是渴望和幻想。它不断地给你饥渴感,却不给你满足感,或者说,它让你产生的饥渴感远大于满足感。此时带来兴奋感的是,不断地进行渴望这一行为或意图,满足感带来的奖赏已经没有渴望更多奖赏这一目标更令人兴奋了。渴望更多替代了获得本身,成了终极目标,也可以说方法成为了目的,过程成为了结果。
把方法论当作认识世界的武器,这是自然选择结束后,从荒野中崛起的人类继续使用工具所发展出来的应然状态。一部分人在使用武器的过程中,则变成了武器的一部分,把武器当成了身处此地的意义,武器成了自我实现的目标,变成了本体赖以生长的唯一,原来的本体则成了新本体的旁枝,成为了铺就道路的工具。
以唯一理想作矢志不渝状,这是长期以来,爱作宏大叙事的社会倾向给予我们的天然加戏,沉浸在骨血里过于深刻以至于成为了潜意识的一部分,成为了赖以认识自己的很大很明显的一个角度。按照大脑在自然选择中消耗更少能量保存更多能量以获取更大生存可能的倾向,其惰性或我们称之为惰性的东西会让我们在习以为常的快车道上一路狂奔,过程无比丝滑,彷佛弹指一挥间,在意识意识到之前,就到终点了。
虽然好像是来过了,似乎,我们却并没有来过。
在咖啡馆里,不远处座椅旁的交谈声会忽大忽小,音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坐在那里的人儿也会消失不见或突然出现,如果不戴眼镜,我就不会知道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现在那个人,TA曾经来过吗?
暖烘烘的咖啡馆此起披伏的交谈声里,使得按着键盘的手有点迟疑,怎么才算真正来过呢?
在空下来的时光这算可以选择的自由里,又有多少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真的自由吗?我真的自由吗?
杯中的咖啡冒着袅袅的热气,这个问题对我们有多复杂对咖啡就有多简单,「此处应补上 宇宙的琴弦关于镜像空间对解决方法简化的部分,待补上」。只要咖啡在认真地冒着热气,它就是自由的。毫无疑问,它总是自由的。即使不能离开水泥浇筑的城市,只能在街道边咖啡馆这逼仄的空间里绽放自己短暂的一生,它的生命也一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