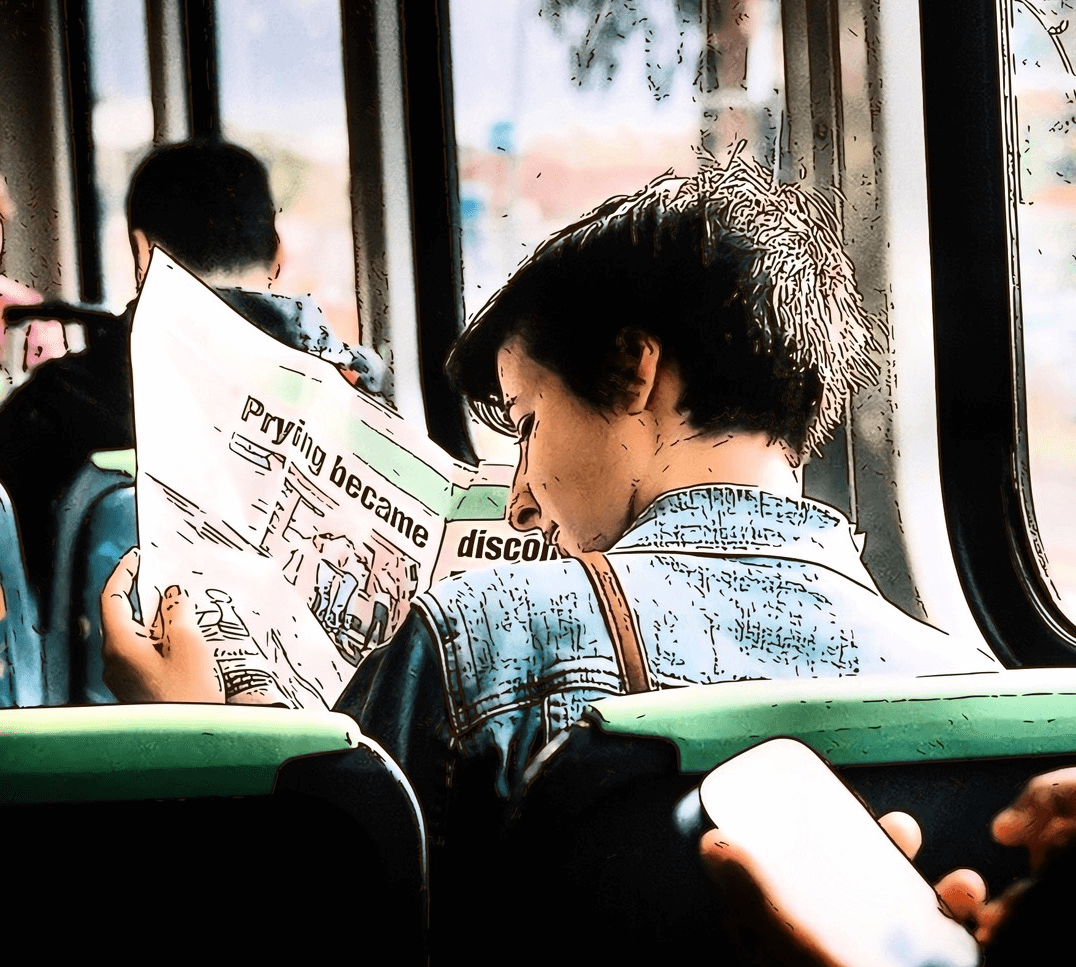白衬衫同学一身修身的西装打扮,手里挽着一个黑色纸袋,从南京西路上星巴克最大烘焙工坊二楼往下走的时候,我正在一楼心不在焉地发短信息。
在这个脑子转不过弯来的瞬间对着楼梯台阶的惊鸿一瞥,伴随着白衬衫同学带着略微的呆滞表情的相向而行,让注意到这位仁兄穿着倍儿讲究的我瞬间觉得自己就像刘姥姥一样土,试图掩饰差点无法面对自己的不讲究的窘迫心态,表情应该有一丢丢不自然。
在二楼还没坐稳多久,白衬衫突然问道:“你觉得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怎么老有人问这个问题?感觉往神棍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一般谈论目的,总是把它与成果之类的词联系到一起,具体到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大多可以推断为提问的人想知道的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有怎样的人生际遇。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神童诗·四喜》
古人把这首诗中的际遇描述为人生四大喜事,多多少少代表了他们对此类问题的看法。现代人的看法虽然复杂得多,大部分情况下与诗中的观点也差不了多少,都聚焦于某一类需要实现的未来成果。远大抱负与其说是为了将来的自己能够更优秀一点,不如说是在内心构建了在未来满足自己当下情感需求的自我期待,也就是常说的心灵寄托。心灵寄托、情感需要和远大目标,是一个东西,它既能帮助人暂时性地逃离无法面对的当下困境,也能激励人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给人无比强大的瞬间信念,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红与黑,罪与罚。
这终究不是现实真正的样子。给自己和他人穿上华丽的貂皮也好,皇帝的新装也罢,自以为能藉此面对世事纷扰。真相却是,一直在与美好的生活斗争的,一直只是只能是——赤条条的自己。
白衬衫同学是背对着二楼那个门的,这让我在交谈的时候得以观察来来往往的人:在柜台里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二楼从其它地方路过的西装革履的物业小哥、拿着装有烘焙好的咖啡豆袋子安坐的小伙伴一群还有在我身后不断拿着手机拍烘焙坊全貌的一对小情侣。
接着和白衬衫讨论之前在北京西路某家素菜馆提到的管理类书籍话题,那时候虽然看了一些经管书,但不及德鲁克套装的影响大,说那时在看管理类书籍的时候,想的都是德鲁克的书。当时看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21世纪的管理挑战》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读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能和《创新公司》、《奈飞文化手册》、《这就是OKR》还有
之前因为在社交沟通上总觉得有困难,在沟通类书籍上用了较多精力(现在沟通能力依然欠佳,请多多包涵),初次看管理类书籍,总觉得很繁琐机械,似乎没有灵魂。看着看着,在个人理解中,管理类的书和心理沟通的书,在讲的东西的本质上,好像也变得差不多了,这使得读起管理书籍来就像是在走一条熟悉的街道,轻车熟路。
沟通类书籍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的不透明,合作内容以及意向的信息不透明,给了双方产生未知情绪(比如坐立难安、盲目自信)的空间,情绪信息的不透明进一步扭曲双方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就同一议题达成更合理沟通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谈判力》这本书之所以很难得到良好实践,是因为他假定双方都是理性人,根据给定的信息判断并博弈。现实却是,由于信息不透明导致的人心不稳,使得谈判(或者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充满了以情感需求为附随目的(如果不是主要目的的话)的大乱斗。这也是为什么《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要强调,在沟通过程中要识别出对方真实的情感需求。情感需求即使没有在纷纷扰扰的沟通中成为最大的怪兽,至少也是比本质需求小不了多少的干扰因子。
管理是作为实现组织宗旨的工具存在的,这一工具在做出决策的环节需要以当下掌握的信息为基础进行判断。管理者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实现信息在交互反馈过程中的透明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朝着组织的宗旨迈进。德鲁克写书的时候,还是传统企业大行其道的时期,企业内部信息沟通方式还有福特汽车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遗留特点,受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影响很深。在当代,皮克斯动画、英特尔、Netflix和Google力图实现企业内部更坦诚的沟通,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耗这一更深层次的需求使得管理者无比强调坦诚相待的重要性,《创新公司》里管理者为了让所有工作人员诚恳对待彼此的意见付出的努力让人印象深刻。管理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制度,根本原因就在于,使管理赖以存在的土壤各有不同,使管理有效的信息千变万化。同样规模的组织,类似的宗旨,类似的员工结构,完全相同的管理基本无法产生相同的成效(更何况,对于成效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信息(打这个字的时候,特别想把——“你们都是弟弟”——打进来,别问为什么,脑洞比较大。)
正在唾沫与孤鹜齐飞的时候,烘焙坊的工作人员开启了全面收拾桌椅模式,暗示在座的各位可以走人了。我们识趣麻溜地走下了旋转楼梯,在深夜的街头找到了恒隆广场两个写字楼之间的长凳,虽然很咯屁股,义无反顾地坐了下去,很凉。
在<Thinking ,fast and slow>里,作者指出,人们通常寻找一个Anchor用来作为参照物形成初步的认识,在不断修正后做出判断。和这个机制类似的现象是,相对于抽象完备的理论,人们更容易从一个着力点发力理解全局。表现在曾鸣的《智能商业》里,就是“点线面体”,这个比喻相当直观,是一个很便利理解他试图表达内容的角度。虽然这个比喻很直观,我的观点是:作者提前设立的用来便利思考的工具妨碍了读者从更本质层面理解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曾鸣作为行业大佬在这本书里没有把他更丰富的知识和积淀用更有技巧更精湛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没有批判的意思,只觉得还有更好的表现手法)。这个论点表现在《人人都是产品经理》里面则是,作者提到的“大产品”,看起来不像是为了产品而产品,更像是为了“大产品”而“大产品”,为了解释概念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思考的角度,但这不是事物的本来样子,这些只是衣服。
Eric Schmidt在
就如我们,有时候会陷在自己编织的美好愿景里,把那些东西当成自己的意义所在。
白衬衫问:“人是为什么活着的呢”,总得有个目的嘛不是。
真理永远能通过千千万万个角度展现自己的智慧之光,而受制于语言和思维的局限性,我们无法用文字把真理表达如它本身一样完美,在此借助一下麻省理工系统动力学这一思维工具,把个人理解下的生活的目的做一番解释。
站在超级观察者的角度,在世界这个大的动力系统里,人们每一步的行为,都会产生以该行为为中心的下一个反应,顺着这个反应,人们又会做出下一个各自不同的行为,以时间为线索向前拉伸向后推进的话,就是像是一幅层层递进的循环图,以一天为线索,离开家的,最终又回到家里,以一年为线索,在离家归家的小循环里做圆圈运动的人们,又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轨道上成为一个环节,甚至,一根琴弦。
正是由于这种动态性,或者绝对的运动,或许使得向远处看从思维角度的一个小部分成长为很大的思维怪兽,因为足够简单笔直、毫不费力。
并不是说不需要看向远方,而是说搜集近处和远方的信息,目的都在于走好现在的每一步,毕竟,我们能做出的选择只存在于当下的时空里。无论是沟通还是组织管理,抑或OKR工作法,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都只是做出选择的参考因素,如果从参考因素异化为情感需要、心灵寄托甚至是支撑人走下去的唯一信念,这些异化的信息就无法保证我们始终能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举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发生过多次更迭)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白衬衫的问题就很好回答了。
天赋、资源、历史伤痛、当前困境、远大愿景,都是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参考信息,生活的目的,就是在所有这些参考信息的围攻下,在当下,做出最好的选择,更准确的说法,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从而塑造我们自己的更好的现在。在这里,没有未来。
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西西弗肯定也是基于所能得到的信息,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在这里,努力、拼搏、愿景、信念,这些都成了精神胜利法,伟大的人不需要伟大这个词,一直在努力的人也绝不需要努力这个词来激励自己。认真生活的人没有浪费时间寻找目的,他们活着本身,就是目的。